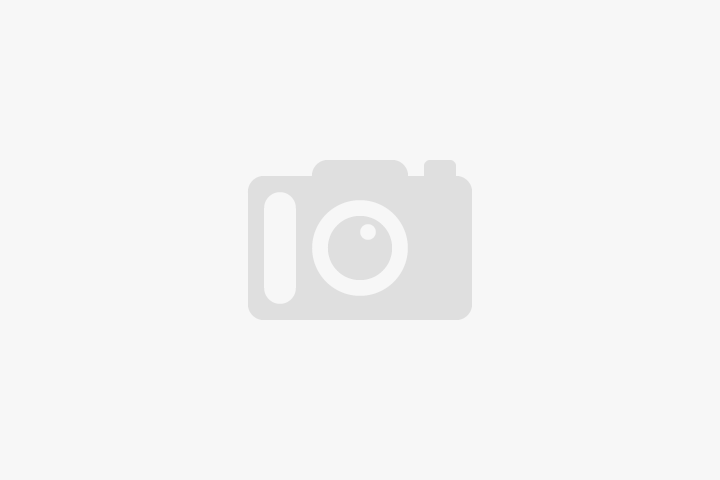微信扫一扫
危急关头:沉默的殡葬业与职人尊严
“逝者的体面”,正以严酷的方式敲打着人们的神经,以至于有人已经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寻找出路。更多人则沉默着面对一场“殡葬堰塞湖”。
上海浦东某小区,一位居民在邻居群里发了一段话,大意是:他的父亲于3天前去世了。这位居民细数自己已经通过能想到的所有途径,都没有能够将父亲的遗体转运出去。于是,他向邻居们宣布:准备“在本小区自行找块空地焚烧尸体”、“居民们如果有意见,请选择报警”。
这位居民当然不可能真的在小区焚烧遗体。发出这样的信息更多是万分无奈之下的情绪表达,也是希望借助社会关注来寻找解决方案。
在很多人面临急难时,“黄牛”趁乱倒卖殡仪馆的号源,让原本壅塞的通道雪上加霜。12月末,上海警方抓捕了20多个“黄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殡仪馆面临的困境。
一个月来,在压力之下拼命工作的,除了医生,警察,也有殡葬人。媒体对医院和医生的报道很多,但因为种种原因,关于殡葬承压的公开信息却很少。人们只能通过网络世界里的个体叙事触碰到一次次悲鸣。
殡葬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行业,它承接了人生命尽头的体面。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就高度重视围绕“死亡”的仪式。但出于中国文化的禁忌,大部分人不愿靠近,也不愿轻易提及它。可以说,这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职业。
过去,殡葬人平稳地处理着一个个死亡事件,以至于很多人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而眼下,当困境浮现,我们或许需要重新看看一些年轻的殡葬人正在做些什么。看看这群在社会评价上被压抑的人,在走向赢得 “职业人士”尊严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悲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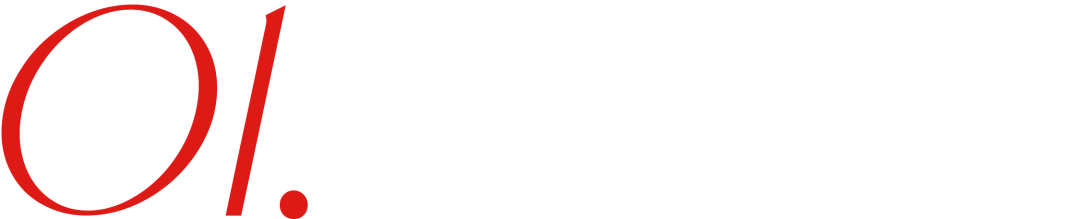
一些微弱的、
关于尊严的努力
石慧的手机里,很少传来好消息。
“姐姐,我只有一个妈妈,她走了,我就变成孤儿了,拜托你让她走得体面些”,电话里的哭声来自一名年轻男子。接这通电话时,摆渡人殡葬公司总经理石慧正带着员工们在上海某医院太平间内接应遗体。太平间内的工作十分繁忙,她简短安慰了男子以后,就为他的微信简短备注名字和母亲去世地点:“某某某,某某医院”。
忙碌间隙,石慧向我打开手机通话记录,拉下公司在过去24小时内接到的电话:近300个。大部分电话最后都会化为一个简单备注。她的同事则会立刻向逝者家属发去从如何办理殡葬事务的全流程,也包括在家中保存遗体的技巧。
此前,因为出现过“黑殡葬”趁乱加价的事情,他们还会尤其叮嘱来电者不要受骗,“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一条龙’、香烛店收取加急费可以插队的话”。
每一次接通电话,石慧都要做好听一个悲伤故事的心理准备:
家里70岁的老人走了,来电请他们办丧事的竟是90多岁的老母亲,老人没有手机,留的是座机号码。她无法预约殡仪馆的号,只能请殡葬公司代劳,很难想象,接下去,老人还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70岁的父母同时去世,他们的儿子已经陷入奔溃;
一位外籍华人的亲人过世,要办死亡证明。因家已经拆迁过,户口都不知道落在哪里,找不到户口就办不了证明。居委会、派出所都有工作人员病倒,没办法帮他及时查到,最后还是12345帮他解决了问题。在20分钟里,这个焦虑的男人向石慧的同事打了十几个电话,每接一次电话,这位同事都要说服自己耐心地、一点点告诉他,下一步该如何操作。
也有人的情绪正处于临界点上,一点就着,会忍不住把对流程的全部不满都倾倒在殡葬公司身上。
“一个人是十几个电话,我们每天面对多少人?任何有七情六欲的人都可能无法承受,”但石慧也理解:在资源特别紧缺的时候,人更容易依赖眼前仅能找到几根稻草。这个时候,他们意外地成了一根的稻草。
几天前,“90后”职员施小琳接到一个同龄女孩的电话,父亲还在ICU抢救,女孩已经在筹办后事,她不断恳求施小琳帮帮她。其实,施小琳能做的也很有限,而电话那头的人其实是在寻找心理安慰。女孩的处境让施小琳一次次联想到自己,“如果我也遇到这种事,要怎么办?我很少上医院,父母都健康,但她却要面对爸爸去世”。一种发乎本能的同理心,催促施小琳尽可能帮助她。她花了很多时间去宽慰女孩,仔细交代了筹办后事的步骤,还一直在微信上回答她的问题。

最终,来电询问的很多人并不会成为摆渡人的顾客。一个多月来,殡葬公司的服务空间也是大大压缩,只剩下几项最简单的项目:闪送寿衣、制作遗像、设置灵堂,以及后续的祭烧服务。但石慧和她的同事们尽力用自己获知的全部信息去指导这些陌生人。
“说到底,现在太多人面临困难了,看到那么多无助的人,难道不管吗”,石慧说。
公司里有年轻女孩刚刚进入殡葬业,受不了接踵而至的抑郁故事,接了几天电话,哇哇哭,边哭边说:“太可怜了,帮帮他们吧。”
吃饭的时候,大家聚到了一起,气氛稍稍活跃,女孩们又开始能够说笑几句,可在一线与遗体和逝者家属打交道的男生始终沉默不语。石慧说,哪怕人手再紧张,她都会每天召集至少一组一线员工回公司开会,“为的是吸掉他们的负面情绪”。
连轴转的石慧不时会感到一阵心口痛。在她黑色羽绒服的口袋里,一直装着一瓶丹参滴丸,和一瓶速效救心丸。

被压缩的仪式
社会急转弯处,个体的“体面”被压缩了。
在上海,按一般流程,从开具死亡证明到追悼会的流程,大约相隔3-5天,郊区可能需要7天。而到落葬、“做七”这个步骤,则更长。现在,很多殡仪馆已经无法开追悼会,家属需要尽量压缩最终告别的时间。很多情况下,这个时间仅有几分钟。
摆渡人原本是一家以仪式策划为主的殡葬公司。他们希望通过仪式,给逝者一个体面的谢幕,也给家属带去安慰。在完成仪式的过程中,公司需要和家属深入沟通,了解逝者的人生经历和整个家族的历史。但最近这段日子,一切过程都在朝着最简化的方向走。他们的工作内容也一下子变了。公司职员每天与家属沟通最多的,已经不再是商量着去策划一个体面完满的仪式,而是一套基本流程,比如,办理死亡证明,联系殡仪馆等等。
这主要是由于殡仪馆暂时面临的困境。一般情况下,上海15家殡仪馆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置这座特大型城市正在发生的死亡。可如今,殡仪馆的火化速度和存储设备无法满足需求。雪上加霜的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也感染新冠病毒,身体无法支撑工作。

◎图 人类学家袁长庚曾在南方科大开设“死亡课”
在殡仪馆发生的拥堵,落到具体的家庭,后果就是,尸体可能滞留在家中或医院,无法像以往那样快速转运,很多接运尸体的日程都已经排到4天以后。
少数“黑殡葬”开始趁乱加价。他们的套路是,承诺家属付一笔加急费,就能让殡仪馆提前转运。石慧指出,“加急费”并没有多少实际用处,殡仪馆面临着统一的政策,无人有权“加塞”,插队提前转运。这些“黑殡葬”也没有特殊门路,他们只是派“黄牛”每天一大早去殡仪馆排队抢号。如果排不到号,就是拖延家属的时间。
石慧和同事们也时常会遇到这样的发问,“为什么我们家不能快速转运?钱不是问题,我多给你们钱,行不行?”这是一个考验职业操守的时刻。“如果选择加价,那么我们坚持的一些原则就没有了”,石慧说,她会明确告诉家属“不可能”。
但他们也遗憾地发现,不少人还是会相信“黑殡葬”的话,心甘情愿付钱,甚至主动要求再加钱,为的是让逝者走得平稳些。
面对因遗体无法转运而焦虑万分的家属,石慧也会这样安慰他们:“从传统习俗来说,亲属是需要守灵的,遗体应该有个停留的时间,生者也该有心理上接受的过程,而不是马上进冰箱、火化。”
以更长的时间维度看,逝者家属的焦虑,与现代社会处理“死亡”的节奏大大加快有关。一旦这个流程有了阻滞,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极端的非正常状态。人们已经习惯于一种新节奏——在一周内送走逝者。可在传统社会,普通人家都有停灵三天的习俗,处理“死亡”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种传统离我们并不远,只是,它正以极快的速度消散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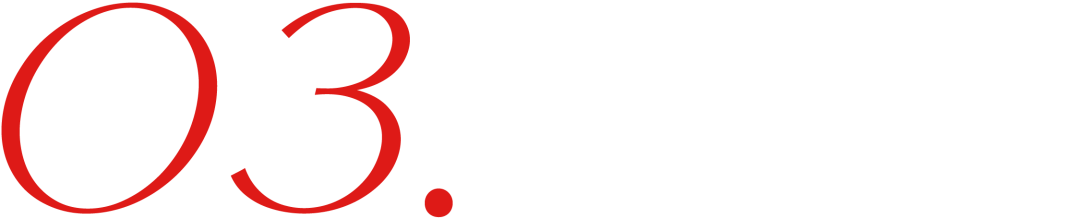
变化中的行业
与依然沉默的人
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人们越发关注“老去”和“死亡”的问题。这两年,影视、出版和传媒业也在不断推动着人们对“死亡”意义的重新思考。但来自殡葬人声音付之阙如。
大部分殡葬人习惯于沉默。让他们沉默的主要原因,还是文化禁忌。用殡葬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被骂怕了”。
“自古棺材铺不打广告,别的行业都能打广告,我们不行”,施小琳会做一些对外文案的发布工作,对舆论变化很敏感。她性格外向,快人快语,但在处理公众号文章时,她几乎没有直接落笔的时候,每次都要考虑到各种限制因素,以曲笔写出来。
在小红书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与殡葬有关的内容,会被限流。哪怕是一些关于理解“死亡”的文章,或是公益性的科普贴,收到推送的读者也会直呼“晦气”,甚至直接开骂。

◎图 建筑师安藤忠雄在日本北海道一座墓园中设计的“头佛”
看到这些留言,施小琳会感到不公:同样是没日没夜工作,一些岗位上的人会被大家歌颂为“奉献”,但轮到殡葬人,很多人的评论马上就变成了“为了钱,命都不要了,哪怕,我说自己今天吃了顿不错的西餐,也有人会说,赚‘死人钱’,才能支撑高消费”。
“为什么轮到我们,所有说法全都反过来了,都是以负面的眼光看待我们?”
诚然,人们对殡葬人的误解,来源于行业自身存在的痼疾。“暴利”是人们对这个行业最多的指责。不少殡葬公司的职员也承认,某些环节存在着“暴利”。最典型的就是骨灰盒,利润可以高达数十倍,其次是寿衣等物品。这也是骨灰盒的特殊性导致的,一个骨灰盒需要在地下长久存放,因而它的木质、雕工都有很大的伸缩空间。
而丧葬用品的特殊性还在于,只要卖家动用一些话术,顾客就不会讨价还价。钱来得太容易了。这致使行业中一部分人将“骗家属掏更多钱”与“业务能力”划上等号,并沾沾自喜。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一部分殡葬公司来说,只要手握“尸源”,就不愁没有生意。
但人们可能忽略的一点是,殡葬行业也在发生很大变化。在“生死观”的更迭中,新一代对殡葬仪式流程的要求也全然不同了。
过去,人们更看重的是昂贵的骨灰盒和寿衣或是足够热闹的葬礼带来的体面。在熟人社会中,丧礼的隆重与否,直接关系到周围人对一个家庭的评价。葬礼必须是由社区里的人共同完成的,如果葬礼没人帮忙,不够热闹,说明这个家庭人望很差。而如果葬礼不够隆重光鲜,则说明家庭成员不孝或凉薄。这些都是一辈子洗刷不掉的耻辱。
但在原子化的社会,有关婚丧嫁娶的仪式都变得逐渐个人化,主角不再是家族和社群,而是逝者与至亲。对葬礼,人们看重的,也不再是功能性地对外展示,而逐渐变成了向内的情感探求。更多人希望通过仪式来固定一种私人情感联系,并由此保留一份回忆。
葬礼开始成为一种心理上的归依。一个从日本逐渐传入中国的风气是,一些人开始为自己筹办身前葬礼,也是为了在社会关系中寻求心理归属。
一部分殡葬公司开始回应新的社会风尚。他们正脱离传统老旧的业务模式,不是盘算着围绕昂贵的物品做“二道贩子”,而是在礼仪的设计中铺设更多的人力,注入更多人文关怀。
切入点的变化,带来业务模式的重塑。比如,在逝者离去后,会有“设灵堂”、“供饭”的步骤,一些殡葬公司会劝说家属免去这个环节,因为设灵堂、撤灵堂,需要殡葬公司的员工来回跑两次,成本很高,收费却不会很高。但如果着眼于仪式的完整性,殡葬公司会劝说家属设灵堂、供饭。这是一个缓缓接受亲人离去的过程。
筹办一个好的仪式,需要殡葬人非常深入地了解逝者和其家族。而每一位逝者经历不同,家人对逝者的情感也不同,这都需要执行者通过仪式将之表达出来。对于策划者来说,每一次葬礼都有独特的意义需要表达,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拷贝。与婚礼策划不同的是,人们可能会用3个月到半年时间筹办一场婚礼,而留给葬礼的时间通常只有几天。
行业发生的种种转换,意味着殡葬人需要有更好的教育背景,更全面的技能和更高的自律精神。也就是说,殡葬人同样应当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人士”。
※※※※※※
“人们可能认为殡葬业是黑的,但总有一点白,只要能看到亮光,就值得我坚守”,谈起自己的职业选择,年轻的施小琳说。
不光是殡葬行业,某种职业被短暂“污名化”的事例屡见不鲜,它曾经发生在女销售、女公关,以及教师和医生身上。这种偏见,最终会伤害每一个人。只是殡葬业更为特殊,被“污名化”的历史更长,且至今面临困局,因而可以被视为职业伦理从传统转入现代的一个缩影。

而施小琳的话,也代表了很多职场人对职业的看法,即,在选择一份工作的同时,也把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之联系在一起。
关于“我们为何而工作”?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职业精神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观念,它源于 “天职观”,即“所有的职业都带上神圣的光环,有着超越功利的意义。人们不再把职业仅仅当成一个饭碗、一种谋生手段、一种权宜之计,人们不敢轻视任何职业,对于各种职业都怀着虔诚的态度,敬业精神由此而来”。
这套“天职观”虽然源自基督新教,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世界各个角落带来了深浅不一的影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人的敬业精神,不单靠自驱,也需要外界同样抱着“虔敬的态度”来看待自己,否则难免枯竭。在一个对专业缺乏尊重的环境里,是很难生长出集体性的敬业精神的。而一旦敬业精神被破坏,余下的就只能是功利算计和一套权宜之计。在职业偏见的“鄙视链”里,没有高人一等的赢家。
-
上一条:国家倡议红白事尽量简办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